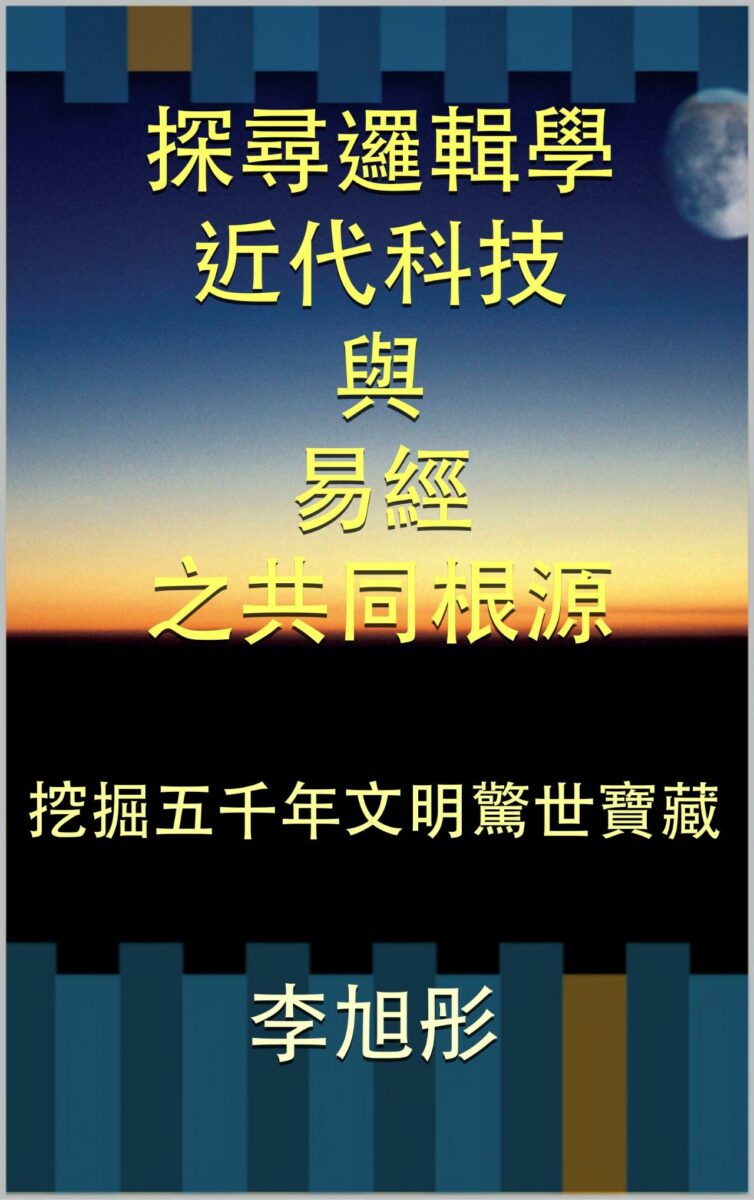引言:一场声势浩大的“反诈战争”,为何始终打不到源头
近年来,中国社会被持续卷入一场高强度的“反电诈”动员之中。官方宣传铺天盖地,从校园到社区,从银行到通信网络,“反诈”成为一种全民政治正确。然而,吊诡的是,在监管力度不断升级、个人行动空间不断被压缩的同时,跨境电信诈骗,尤其是所谓“缅北电诈”,并未被结构性消灭。
这引出了一个始终被回避的问题:
如果诈骗高度依赖通信网络规模化、自动化运行,为什么反诈的成本几乎全部由普通民众承担,而不是由通信系统本身承担?
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(FCC)近期针对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发出的 RMD(Robocall Mitigation Database,反自动拨号骚扰数据库)合规命令,意外地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对照样本。
第一部分:RMD 是什么——它并不“反诈”,它“问责”
1. RMD 的制度本质
RMD 并不是一项宣传政策,也不是执法运动,而是一套通信责任认证机制。其核心逻辑只有一句话:
谁提供通信通道,谁就必须为该通道产生的风险负责。
在 RMD 框架下:
- 运营商必须向监管机构声明并证明:
- 其网络已部署反自动拨号、反号码伪造的技术措施;
- 能够识别、限速或阻断异常呼叫;
- 不会成为骚扰电话或诈骗电话的放行源头。
- 未完成认证的运营商,将被剥夺互联互通资格,其呼叫将被其他运营商直接拒绝。
这是一个硬约束机制,不是倡议,也不是配合执法。
2. RMD 管的不是“骗子”,而是“系统漏洞”
RMD 并不关心诈骗分子躲在哪里、使用什么话术,它只关心三件事:
- 号码从哪里来;
- 流量如何进入主干网络;
- 谁为异常流量负责。
这正是当前中国反电诈体系中最刻意回避的层面。
第二部分:如果中国引入 RMD,会发生什么?
(一)电诈的“工业化基础”将被直接摧毁
缅北及其他跨境电诈并非“零散犯罪”,而是一套高度工业化的系统,其核心依赖:
- 虚拟号码池;
- SIP 中继和国际回拨;
- 自动拨号系统;
- 与中国主干通信网络的稳定互联。
RMD 的制度效果,恰恰是逐条切断这些条件。
制度效果示意:
- 虚拟号码 → 必须登记用途 → 大规模诈骗号池失效
- 自动拨号 → 必须认证、限速 → 高并发能力消失
- 跨境通道 → 可被直接封堵 → 成本暴涨
最终结果是:
电诈将退化为小规模、低效率、不可扩展的犯罪形态。
(二)反诈治理重心将发生根本转移
如果 RMD 在中国落地,反诈的责任链将被彻底重写。
制度对比图:现行反诈模式 vs RMD 模式
| 维度 | 中国现行反诈 | RMD 模式 |
|---|---|---|
| 风险假设 | 群众容易受骗 | 通信系统可被滥用 |
| 治理对象 | 个人用户 | 运营商与通道 |
| 核心手段 | 冻卡、限额、实名、连坐 | 技术认证、限流、断联 |
| 责任主体 | 个体自证清白 | 系统自证合规 |
| 成本承担 | 普通民众 | 通信运营体系 |
| 治理性质 | 行政动员 | 技术监管 |
这不是“反诈力度”的问题,而是治理方向完全相反。
第三部分:为什么中国“完全能做”,却始终不做?
(一)技术能力不是障碍,恰恰相反
中国三大运营商拥有:
- 全球最大规模的通信网络;
- 对国内外号码、信令、路由的完全掌控;
- 成熟的 AI 流量识别与异常检测能力。
不存在任何技术不可行性。
(二)真正的障碍在于:RMD 会打破三条“安全边界”
1. 它会否定当前的“反诈叙事”
RMD 一旦实施,等于承认:
电诈不是因为群众警惕性不够,而是因为系统长期放行异常流量。
这将使现有的宣传逻辑难以自洽。
2. 它会迫使国有运营商承担实质责任
RMD 不是“配合执法”,而是:
- 合规失败即违规;
- 违规即影响业务;
- 业务受限即触及利润与问责。
这将把反诈的压力,从社会底层,转移到体制内部。
3. 它会削弱“反诈”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功能
当前反诈措施的一个显性效果是:
- 强化实名制;
- 扩展数据调取;
- 合理化对个人通信、金融、出行的限制。
而 RMD 的治理对象是机器、通道、系统,而非个人行为。
第四部分:FCC 对中国运营商施压的“镜像意义”
FCC 要求中国移动、中国电信、中国联通证明其 RMD 合规性,本质上是在说:
“如果你的系统可能成为诈骗或骚扰的源头,你就没有资格接入我们的网络。”
这与中国国内的反诈逻辑形成鲜明对照:
- 美国:限制系统 → 保护用户
- 中国:限制用户 → 放过系统
这并不意味着美方“更道德”,而是说明其监管目标更清晰:
通信风险必须在系统层面被消化,而不是转嫁给个人。
结论:RMD 是真正能反电诈的工具,但它不符合现行治理逻辑
综合来看,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结论:
- 在中国国内引入 RMD 类机制,
将对跨境电诈产生立竿见影、结构性、不可规避的打击效果; - 它能从源头压缩诈骗产业的生存空间,而不是制造“全民防诈疲劳”;
- 但它要求:
- 权力从“约束个人”转向“约束系统”;
- 成本从“社会底层”转移至“通信体系内部”;
- 反诈从政治动员回归技术治理。
正因如此,RMD 在中国并非“不可行”,而是不可用——
不是因为它无效,而是因为它太有效,却不服务于当前的治理目标。